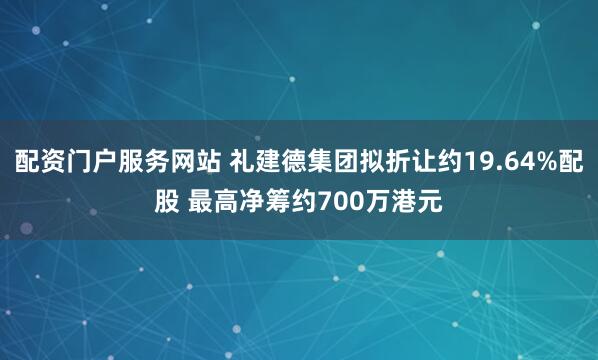祖父的老算盘静静卧在樟木箱的绒布上,乌木框子被岁月浸成深褐色,像块沉淀了百年的墨。十三档算珠,上二下五,紫檀木的珠子边缘磨得浑圆炒股配资平台知识,凑近了看,能瞧见无数细密的指痕,像被时光吻过的印记。
第一次见它,是在祠堂的供桌旁。那年我七岁,跟着祖父给族里的老人算田租。他戴着老花镜,手指在算珠上翻飞,“噼啪” 声在肃穆的祠堂里荡开,惊得梁上的燕子扑棱棱飞起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,在算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祖父的指腹沾着点滑石粉 —— 那是为了让拨珠更顺滑,他总说 “算盘也怕生涩,得顺着它的性子来”。
这算盘是曾祖父传下来的。晚清时他在镇上开粮行,这十三档算盘就是账房里的 “镇店之宝”。粮行收粮时,算盘声能从清晨响到日暮,曾祖父的手指比祖父更快,算珠碰撞的脆响里,混着粮袋摩擦的 “沙沙” 声,像在数着仓廪里的谷粒。祖父说,有年饥荒,曾祖父用这算盘核对着赈灾的粮食,算珠拨得慢,指节都泛着白,最后算出的数目分毫不差,连县太爷都竖了大拇指。
算盘的横梁上刻着道浅痕,是祖父年轻时不小心磕的。那年生产队分粮食,他蹲在晒谷场的石碾旁算账,算盘没放稳,摔在石棱上,横梁裂了丝缝。他心疼得用棉布裹着,连夜找木匠修,木匠用鱼鳔胶黏合后,他又在上面缠了圈细铜丝,说 “这样才结实”。后来那道痕成了他的 “标记”,算账时总爱用指尖摩挲着,像是在跟老伙计打招呼。
展开剩余59%我学算盘时,祖父总让我先练 “指法”。“拨珠要像拈绣花针,” 他捏着我的手指,教我用拇指推下珠,用食指挑上珠,“别用蛮力,算盘记仇,你对它狠,它就算不对数。” 有次我算错了账,急得用拳头砸算盘,珠子 “哗啦啦” 乱晃,祖父没骂我,只是重新摆好珠子,说:“你看,算珠复位了,账也能重算,人这一辈子,错了也能改。”
算盘的底框藏着个秘密。去年整理祖父的遗物时,我在框子的夹层里摸出张泛黄的纸,是 1958 年的工分账,上面的数字用毛笔写得工整,末尾有祖父的签名,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算盘。那时他刚二十岁,在公社当会计,这张纸该是他用这把算盘算出的第一笔账。纸边卷着毛,却依旧平整,像被人反复展看过。
现在这算盘摆在我的书房。偶尔我会拂去上面的薄尘,拨弄几下珠子,“噼啪” 声里,仿佛能听见晒谷场的蝉鸣,看见祖父蹲在石碾旁算账的背影。女儿好奇地问:“这是什么呀?比计算器还慢呢。” 我让她摸摸算珠,说:“这上面的每道痕,都是日子算出来的数,慢是慢,却一分一厘都错不了。”
暮色漫进窗时,算珠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横梁上的铜丝早已氧化发黑,却依旧牢牢护着那道旧痕。忽然明白,这百年的算盘从不是冰冷的器物,它是光阴的秤,称过仓廪的丰实,称过岁月的厚重,也称过一代代人心里的踏实。那些 “噼啪” 作响的算珠,算的哪里是数字,分明是一厘一毫的认真,和一点一滴的日子。
窗外的风穿过竹林,沙沙作响,像谁在轻轻拨弄着算珠。我望着那十三档紫檀木珠子,忽然想,祖父和曾祖父的指温,大概早就渗进了木头里,化作了算珠的魂,在每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日子里,轻轻提醒着 —— 日子要像算珠,落位清晰,心里才能亮堂。
发布于:湖北省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